啟功親述父親死後的怪異事,他皈依的是藏傳佛教
啟功口述歷史(節選)——
我父親死後家裡也出現了一些怪異的事,也請讀者能正確理解:這些事說明我們家那時緊張到什麼程度。

圖片轉載自sepsismd的博客(下同)
我們當時住在什錦花園一個宅子的東院,我父親死在南屋。南屋共三間,西邊有一個過道。我父親死後誰也不敢走那裡,老傭人要到後邊的廁所,都要結伴而行。據她們說,她們能聽到南屋裡有梆、梆、梆敲煙袋的聲音,和我父親生前敲的聲音一樣。還有一個老保姆說,我父親死後的第二天早上,她開過我父親住的屋子,說我父親生前裝藥的兩個罐子本來是蓋著的,不知怎麼,居然打開了,還有好幾粒藥撒在桌上,嚇得她直哆嗦。也難怪她們,因為這個院裡,除了襁褓中的我,沒有一個男人了。於是我母親帶著我們搬到我二叔祖住的西院,以為那邊有男人住,遇事好撞撞膽。我二叔祖很喜歡我父親,他住在這院的北屋。搬去的那天晚上,他一邊喝酒,一邊哭,不斷地喊著我父親的名字:“大同啊,大同啊!”聲音很淒慘,氣氛更緊張。到了夜裡,有人就聽到南屋裡傳來和弄水的聲音,原來那裡放著一只大水桶,是為救火准備的,平時誰也不會動它。後來一件事更奇怪。我二叔祖有一個孩子,我管他叫五叔。他的奶媽好好地忽然發起了瘋癫,裹著被褥,從床上滾到地上,嘴裡還不斷念叨著:“東院的大少爺(指我父親)說請少奶奶不要尋死。還說屋裡櫃子的抽屜裡放著一個包,裡邊有一個扁簪和四塊銀圓。”我母親聽了以後,就要回東院找,可別人都嚇壞了,攔著我母親不讓去。我母親本來是想自殺的,連死都不怕,這時早就豁出去了,沖破大家的阻攔,按照奶媽說的地方,打開一看,果然有一個扁簪和四塊銀圓,跟著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其實出現這些怪現象必然有實際的原因,只不過那時大家的心理都被恐懼籠罩著,一有事就先往怪處想,自己嚇唬自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而這正是一個家族衰敗的前兆。我從小就是在這種環境和氣氛中成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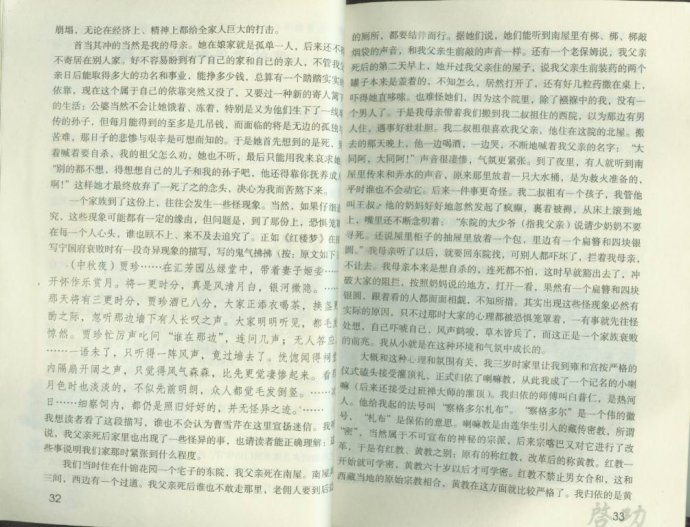
大概和這種心理和氛圍有關,我三歲時家裡讓我到雍和宮按嚴格的儀式磕頭接受灌頂禮,正式歸依了喇嘛教(正式名稱應該為“藏傳佛教”——看雪客注),從此我成了一個記名的小喇嘛(後來還接受過班禅大師的灌頂)。我歸依的師傅叫白普仁,是熱合人。他給我起的法號叫“察格多爾札布”。察格多爾是一個佛的徽號,札布是保佑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蓮華生引入的藏傳密教,所謂“密”,當然屬於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後來宗喀巴又對它進行了改革,於是有紅教、黃教之別:原有的稱紅教,改革後的稱黃教。我歸依的是黃教,隨師傅學過很多經咒,至今我還能背下很多。
我記憶中師傅的功德主要有兩件。一是他多年堅持廣結善緣,募集善款,在雍和宮前殿鑄造了藏傳黃教的祖師宗喀巴的銅像。這尊佛像至今還供奉在那裡,供人朝拜。二是在雍和宮修了一個大悲道場,它是為超度亡魂、普渡眾生而設立的,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悲咒,喇嘛、居士都可以參加,我當時還很小,也坐在後面跟著念,有些很長的咒我不會念,但很多短一點的咒我都能跟著念下來。一邊念咒,一邊還要煉藥,這是為普濟世人的。我師傅先用笸籮把糌粑面搖成指頭尖大小的糌粑球,再放在朱砂粉中繼續搖,使它們掛上一層紅皮,有如現在的糖衣,然後把它們用瓶子裝起,分三層供奉起來,外面用傘蓋蓋上。這是黃教的方法,紅教則是掛一層黑衣。那四十九天,我師傅每天晚上就睡在設道場的大殿旁的一個過道裡,一大早就准時去念咒,一部大悲咒不知要念多少遍。因為這些藥都是在密咒中煉成的,所以自有它的“靈異”。那時我還小,有些現象還不知怎麼解釋,但確實是我親自所見所聞:有一天,趕上下雪,我在潔白的雪上走,忽然看到雪地上有許多小紅丸,這是誰撒的呢?有一位為道場管賬的先生,一天在他的梅花盆裡忽然發現一粒紅藥丸,就順手揀起,放在碗裡,繼續寫賬,過一會兒,又在梅花盆裡發現一粒,就這樣,一上午發現了好幾粒。等四十九天功德圓滿後,剛揭開傘蓋,一看,滿地都是小紅丸(即“甘露丸”——看雪客注),大家都說別揭了,三天以後再說吧。那些地上的小紅丸大家都分了一些,我也得了一些。這些藥自有它們的“法力”(藥效),特別是對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我小時候還聽說過這樣一件事:溥雪齋那一房的,有一位叫載廉(音)的,他的二兒媳有一段時間神經有點不正常,顛顛倒倒的,他們就把我師傅請來。師傅拿一根白線,一頭放在一碗水裡,上面蓋上一張紙;一頭拈在自己手裡,然後開始念咒。念完,揭開紙一看,水變黑了,讓那位二兒媳喝下去,居然就好了。

我道行不高,對於宗教的一些神秘現象不知該如何闡釋,也不想卷入是否是偽科學的爭論。反正這是我的一些親眼、親耳的見聞,至於怎樣解釋,我目前很難說得清,但我想總有它內在的道理。其實,我覺得這些現象再神秘,終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問題。往大了說,對一個人,它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養,我從佛教和我師傅那裡,學到了人應該以慈悲為懷,悲天憫人,關切眾生;以博愛為懷,與人為善,寬宏大度;以超脫為懷,面對現世,脫離苦難。記得我二十多歲時,曾祖母有病,讓我到雍和宮找“喇嘛爺”求藥。當時正是夜裡,一個人去,本來會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莊嚴的廟宇靜靜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風徐來,樹影婆娑,不知怎地,忽然想起《西廂記》張生的兩句唱詞:“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煙籠罩”。眼前的景色,周圍的世界,確實如此,既莊嚴神秘,又溫馨清爽,人間是值得贊美的,生活應加以珍惜。我心裡不但一點不害怕,而且充滿了禅悟後難以名狀的愉悅感,這種感覺只有產生於對宗教的體驗。對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正確處理好宗教問題大大有利於國家的安定,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和睦。我認識一位宗教工作者,叫劉隆,曾任民委辦公廳主任,他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又作班禅的秘書,協助他工作,關系處理得非常好,班禅非常信任他。他對其它宗教也非常尊重,決不作任何誹謗,一切從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團結安定與共同利益出發。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真正的宗教徒並不受本宗教的局限,他的胸懷應該容納全人類。如果所有的宗教工作者都能作到這一點,我想世界就會太平得多。當然,還有一位我特別尊重的宗教工作者,那就是趙樸老。
再說我的師傅,他在六十多歲生病了,就住在方家胡同蒙漢佛教會中“閉關”,不久就圓寂了。圓寂後在黃寺的塔窯火化。按藏密黃教的規定,火化時,要把棺材放在鐵制的架子上,棺材上放一座紙糊的塔,鐵架下堆滿劈柴,下面裝著油。火化時只要點燃油即可。全過程要三天。他的徒弟中有一位叫多爾吉(藏語金剛杵之意)的,最後把師傅的遺骨磨成粉,攙上糌粑面和糌粑油,刻成小佛像餅,分給大家,我也領了一份,至今還保留在我的箱底裡。別的宗派也有這種習慣,五台山的許多高僧大德死後也如此,別人也給過我用他們的骨灰鑄的佛像餅。
總之,自從歸依雍和宮後,我和雍和宮就結下不解之緣。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宮去拜佛。在白師傅圓寂很久後的某一年,我去拜佛,見到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喇嘛,他還認得我,說:“你不是白師傅的徒弟嗎?”直到今年,兩條腿實在行動不便才沒去,但仍然委托我身邊最親信的人替我去。現在雍和宮內有我題寫的一幅匾額和一幅長聯。匾額的題詞是“大福德相”,長聯的題詞是“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萬億劫之中”,這都寄托了我對雍和宮的一份虔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