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西南隱人
二、寶玉的佛教精神
那寶玉也在孩提之間,況他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如一體,並無親疏遠近之別。(第五回)
寶钗初入賈府時,這段對寶玉禀性的刻劃是很關鍵的。它說明寶玉對人對事擁有一顆平等無二之心。就佛教來說,無分別之心的人在看問題時常走中道,不落二邊見。這類人往往給人一種若癡若愚的外在表現,但在修持上則易獲得上乘菩提。由於內慧根深,在解悟佛法、修持向道的過程中,他們往往采取一體同觀的態度。作品中雖未直說寶玉是一個上根之人,但他後來的行為無處不表現出一個真假相容、亦佛亦道、色空無二的行者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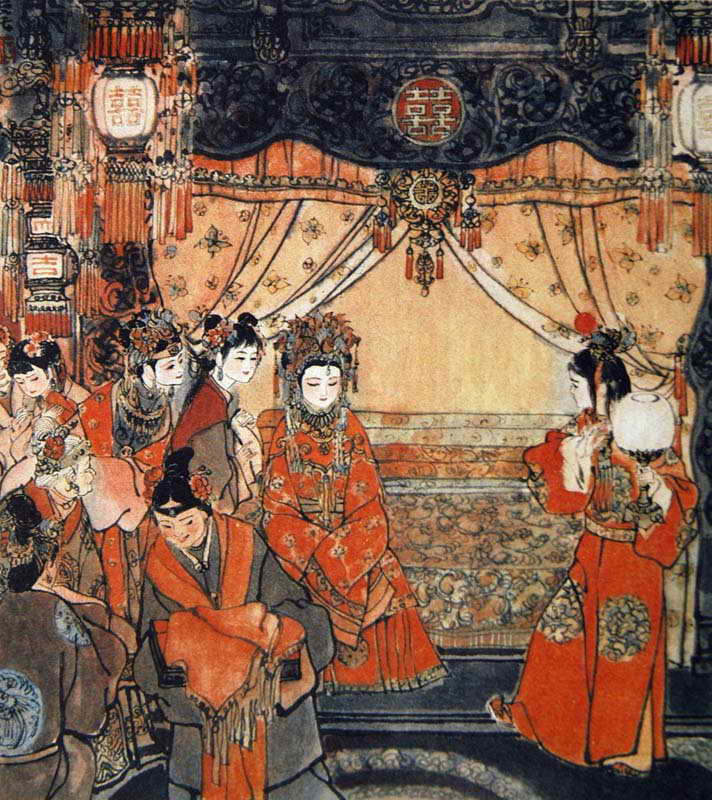
寶玉對別人平等無二,但對自己則擁有一顆出離之心,這一點在第七回他初會秦鐘時的一段自白中便有所表現:“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指秦鐘)!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豬癞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裡,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但绫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寶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寶玉將自己的肉身視作污穢,這其實就是在作一種“不淨觀”。長修不淨觀的人可以培養出一顆出離之心,這也是寶玉初悟禅理的一種表現形式:即非禅之禅,非觀之觀。當然,不淨觀並沒有完全擺脫物我兩忘的境地,它仍然還有物我之分;寶玉也並未停留於此,當他後來發現自己不能改變個人命途時,分別之心逐漸被包容之心所取代,癡笑玩愚、打鬧胡謅也成了鍛煉心性的不自覺行為。寶玉是在肉身與環境俱濁的世間愈磨愈圓融,最後走向自在的。所以我們常說,修大乘者必先入凡塵,即是此理。
第二十二回,那段《寄生草》固然是寶玉開悟的一個機鋒,但這只是一個頓悟的契子。真正使寶玉寫下參禅之谒的原因卻是這一回那段感情糾閣的慚悟過程:即鳳姐暗示眾人:那小戲子很象黛玉。之後,先是湘雲的委曲,鬧著要回去;接著是黛玉的使性,最後又是寶玉的“好心不得好報,”索性什麼也不管了。黛玉寶钗等人怕他癡心不改(其實是漸悟了),才再一次以幻滅幻,將其從深悟中**,回到現實中。
從湘雲、黛玉、寶玉三人在情感理解上的層層失望來看,這一段好似一場普通的感情戲。其實,這才是作者借寶玉從漸悟(三人的無奈)到頓悟(回想到《寄生草》曲文而作谒)的過程而闡示佛法的一種手法。它說明一個道理,即語言是無法載道的,因為語言是掛一漏萬的東西,有語言即有分別,有是非。用語言豈能講清世上真谛?不講了,不爭了,這才是知覺的前提,是覺悟的開端。寶玉回想《南華經》中“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也是作者這一觀點的征引:即語言是一種巧,一種智。但是,絕巧去智尚不為最終覺悟。故黛玉以“無立是境,方是干淨”來開悟寶玉,禅境更進一層。
常言道,小乘立空,大乘空立,佛乘不立,因為成佛者萬德俱足。為了讓寶玉擺脫“無可雲證,是立足境,”的有立之心,黛玉可真謂是以空滅幻,以無立破有立。寶钗則直接引據《壇經》,以六祖慧能的空觀和神秀的有形觀的關系來作比較,對寶玉作進一步的開悟。乍一看,兩個姑娘說是去收了寶玉的癡心,實則無意中讓寶玉這一人物更了空一層,為其日後徹底地解脫、悟正法避邪道作了准備,這才是作品希望達到的目的。同時,它也暗示曹雪芹筆下的女子絕非一般。在這裡,我們既能看到一個個實實在在、有血有肉的現實中的可愛女孩形象,同時又能感悟到她們身上超凡的佛性精神。這是一種很高妙的寫法。
無空不自在,自在無不空。要做到這一點,對於一個生活在凡塵之中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他得時時處處、有意無意地被情感所染、被俗務所磨,直到將心裡的是非欲望全都看破看透才行。如果說《寄生草》一場還只是寶玉這個人物的“他覺”行為的話,那二十七回黛玉“藏花”一場則是寶玉的“自覺”在萌生。他聽完黛玉的 “藏花詞”之後竟也心通不二,感發出這樣一段空漠:
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钗、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钗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將來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
這“一而二,二而三”的反復推求簡直就是作者自己站出來進行直接說教,它完成了寶玉這個人物“辭恩了凡”的境界,主動斷情、斷色,求取解脫之心越發明顯。“自覺”是出家修行大菩提心的基礎,是“覺他”行度的前提。可以說,這為寶玉今後徹底遁入空門作了思想上的准備。當然,寶玉這個人物和讀者一樣,對佛法都需要有一個漸悟的過程,所以作者在寫法上
也采取了回環之筆,通過寶玉向黛玉傾述委曲,將寫“空”的筆鋒再次一轉,馬上又“哥哥妹妹”地刻劃起“情”來。
因此,從《紅樓夢》這部作品中,我們能看到太虛大師後來所倡導的漸教精神無處不在。又如三十一回寫道: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道理。他說: “人有聚就有散,聚時喜歡,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兒開的時候兒叫人愛,到謝的時候兒便增了許多惆怅,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恸。那寶玉的性情只願人常聚不散,花常開不謝;及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沒奈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黛玉還不覺怎麼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房中,長吁短歎。此段是作者借黛玉之心思在闡述無常苦空的道理,並用寶玉這個人物來襯托她強烈的出離之心。表面上看,寶玉在天性上不如黛玉覺悟得徹底,但實際不然。在緊接著的睛雯撕扇一節,寶玉對現世的破壞性是很甚的,而且還蘊含著一種對萬事萬物的悲心:“你愛砸就砸。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有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著玩兒,也可以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別在氣頭兒上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不要讓他物受瞋,這就是一種菩提戒心。初一看,寶玉這個人物性格是前後矛盾的,其實這是為了表現他平等無二的心性,他的天性中比黛玉更徹底、更圓融。這一回的描寫也表明:寶玉這個人物不管其多麼乖張,但他的佛教精神終究不離其思想的發展主線,作者是不會讓他偏離太遠的。
說寶玉“一片愚拙”,這道出了寶玉缺少八難⑤之一的“世智辯聰”。從後來他的行為也說明了這一點:寶玉對仕宦之道、經邦濟世之學不僅痛恨有加,而且天生就有一種厭惡之心。第五回裡,寶玉在榮府想午睡,秦氏引其到上房內間。當他看見《燃藜圖》和那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時候,連在這間屋子都不想呆下去。其厭惡之情,出離之心可想而知。所以,象寶钗這種世智辯聰者是與佛無緣的,寶玉則有此一緣。
三、妙玉為何入魔?
妙玉與黛玉具有相同的根性,兩個自小體弱多病,都必須出家修行方可免除一生病災。所不同的是,妙玉出了家,獲得六七年的清修生活,而黛玉則不然,由於抵不過塵陽的熏習,一生病魔纏身。在這個問題上,黛玉的天性中就缺乏平等心,她的分別心是很重的,有真無假是其特點。所以作者稱其“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比黛玉更甚者就是妙玉了。她的分別心比黛玉更甚,連劉老老喝過的茶杯都不要,嫌其骯髒。黛玉的分別心常表現在行為上,從其常常得罪人方面就可見一斑;而妙玉的分別之心則表現在心理上。心不平等、不淨,就是修上十年二十年也是枉然。妙玉走火入魔是何因?這個問題學術界曾認為:惜春代表“空”,妙玉代表 “色”⑥。其實,妙玉入魔即缺乏心戒的結果。
在坐禅當中走火入魔,這是佛門修者常出現的情況。所謂魔者,乃心之所為;心魔亂性,說明行者在心法上沒有徹底斷相。心魔的形成是因行者染習塵緣而來,從阿賴耶識直接進入末那識造成的結果。入魔走火之人,輕者在夢境、意識界即可見到多種幻相,重者則會在參禅中無法突破八識中的第七末那識,並被一定的幻相所障而認妄為真。妙玉的入魔就屬於後一種情況。
《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凡修行之人都會經歷入魔斷相的過程,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人不管其前生如何,他來到現世,從降生到入佛覺悟這一段,總是在塵世中熏習俗務,時間一長,其意識深處的心藏就會染習二垢,即所知障和煩惱障。密宗將其視為習氣身,是沾染於心識之上的習性和對善不善、種種境的判斷力,是入眠未醒之前夢境中常有之相狀,是必須遠離的“顛倒夢想”。遠在古印度的奧義書時代,那些瑜伽修持者在獲得最高的境界——大梵之前,也指出修行者會目睹許多幻相。如《白淨識者奧義書》就記載得有這樣的文字:
霧,煙,日,風,火,
飛瑩,與閃光,
琉璃,與月光,
此等幻相見,
在修瑜伽時,
先於梵顯現。
奧義書所指出的瑜伽修持幻相是一種遠離塵寰修持所見之幻相,因為真正的瑜伽士大多遠離城市,長期的山林獨處打入阿賴耶識中的也都是些簡單的物相,即“霧,煙,風,火”等,而真正的市鎮人事卻很少見到。
妙玉出家經年,被賣到賈府時已有十八歲,身法持戒是沒有問題的,就連劉老老飲過的茶杯都嫌骯髒,可謂清淨了。但妙玉的心法卻不淨,常落入二邊見,特別是見了寶玉,更是情為之所動了,不象寶玉那樣能做到垢不垢處是清淨。一些修密者容易被其自身的魔境所繞,一當然是持咒的法力不夠所致,二就是菩提戒心被忽略。菩提戒心是圓融無上的大發心,是顯密二宗都強調的。同時,也只有上根之人能利用菩提戒心而化魔入佛,等持宇宙。在這一層上,妙玉沒有突破。再則,由於習氣身的存在,境相入心,加之定力不夠,使妙玉法身被毀。所謂“若不持戒禅多聞,虛假染衣壞法身。”(《坐禅三昧經》)說的正是妙玉入魔的後果。這裡的虛假就是妙玉入大觀園後慢慢被塵緣所染而形成的境相,這些東西慢慢駐染留存於根本識的阿賴耶識中並進而入注末那識產生靈相魔圖。這裡所說的不持戒亦即不持心戒,沒有等持宇宙的菩提戒心,也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的那個不生一切心之本心不淨了。何為法身?——大光明點也。妙玉看到的是強賊,不是自他無二的紫金光明法身佛。
在著魔的當天下午,送妙玉回栊翠庵時,寶玉和妙玉在**館附近聽見黛玉的琴聲,進而又聽見琴弦的斷裂,一種不祥之兆籠罩在妙玉的心頭。對此,寶玉麻木不仁,沒有絲毫反應,而敏感的妙玉則急匆匆要趕回去。妙姑既懂占卜,又會術數,真可謂“世智辯聰”了,不入魔又更待何時呢?在入魔的當晚,身邊的女尼為其在觀音前求得一簽,簽書上說是觸犯了西南角上的陰人。其中一人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陰氣是有的。”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因為大觀園的西南角正好是黛玉的**館。妙玉下午正是從那裡經過時才聽見黛玉的琴弦斷裂的。《易·坤卦》曰:“西南得朋,東南喪朋,安貞吉。”西南為陰之純,東北為陽之純。黛玉陽焰不高,當初進園時選擇西南角的**館是有一定道理的。前面我們說了,妙玉與黛玉有著相同的根性,她所住的栊翠庵正好在大觀園的東北角上,對於十分講究占卜術數的妙玉來說,在這一方安居本身就是一大忌,更不用說修行參禅了。由於有相、有界、有術、有我執、自然也就有這一切所產生的束縛,使行者無法徹底解脫道斷。如果她“無眼界、無意識界”又另當別論,遺憾的是妙玉又熟谙道婆的那套占卜術,就真不該從**館前經過了。
對陰魔的闡述,道家的張三豐也有自己的說法:“理雖融而性未見,故萬物發現凶險,心神恍惚,不能做主。又因外邊無知音道侶護持看守,觸其聲色,驚散元氣,激鼎翻爐,劣了心猿,走了意馬,神不守捨,氣不歸元,遭其陰魔。何為陰魔?……皆因真陽一散,陰氣用事,晝夜身中,神鬼為害。不論睜眼、合眼,看見鬼神來往,即耳中亦聽得鬼神吵鬧。白日間覺猶可,到晚來最難過,不敢靜定一時。我身彼家,海底命主。兌金之戊土沖返五髒氣血,皆隨上騰身。提不著他殺身喪命,真乃鬼家活計也。”這與妙玉的情況是何等相似。
以上是妙玉入魔的原因,我們再看看她入魔的條件。
這天下午,妙玉與惜春在蓼風軒對弈時是很平靜的。無所事事的寶玉到來後情況則發生了改變。寶玉先打诨道:“妙公輕易不出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見妙玉紅著臉不理睬,自覺造次的寶玉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在寶玉的一再干擾之下,妙玉終於動容了,竟下意識站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癡癡地問寶玉:“你從何處來?”清代紅學大家王希廉認為,妙玉的入魔從此開始。他在《紅樓夢回評》中寫道:“妙玉一見寶玉臉紅,又看一眼,臉即漸漸紅暈,可見平日鐘情不淺。此時妙玉已經入魔,夜間安得寧靜?”
“你從何處來?”這一問到不要緊,已經嚴肅起來的寶玉不敢證實是否是機鋒,不好回答,而一旁的惜春則肯定妙玉的問話是機鋒。其實,妙玉鐘情寶玉是明擺著的,只是她與寶玉的親近在情感上剛好慢了半拍,加之自己的身份所限,固然難以和寶玉勾通。所以當聽了惜春的解釋之後,她才恍悟過來,自覺已陷得太深,要趕回庵裡去了。
惜春對妙玉的修持不免估計過高,入魔事發後才明白:“妙玉雖然清淨,畢竟塵緣未斷。”而其“大造本無方,雲何是應住?既從空中來,應向空中去。”之偈更顯其發心之大,非妙玉可比。所以王希廉說:“惜春一偈,真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較之妙玉眼界未淨,即生意識界,遂致心有掛礙,恐怖顛倒夢想,霄淵判絕。” (《紅樓夢回評》)
夜晚,妙玉在禅關中想起白天寶玉的言語“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禅房,仍到禅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捨,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禅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庵中。……”從妙玉的情況來分析,她著的是YIN魔。在著名的《楞嚴經》當中,號稱金剛力士的烏刍瑟摩修的就是化YIN心為智慧火。以火光三昧力,遍觀百骸四肢和冷暖諸氣,最終神光內聚,無礙流通,生大寶焰。這裡的“生大寶焰”即诃陀瑜伽的梵光,佛門的智慧火。“妙玉神不守捨,禅床也恍蕩起來。”妙玉入魔的這一現象,正如海仁法師解經所曰:“人體組織,不外四大;欲心不起,四大調和,欲念一動,舉體發熱,YIN心不息,欲火轉盛。當欲心起時,若能偏觀全身百骸,審察煩惱欲火,從何而起,為起自手足,抑或起自骨髓,如是遍觀暖觸,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欲火自息,而成正定。因定發慧,故能神光內凝,修行至此,便可化多YIN心,成智慧火。”
就妙玉入魔一事,反映出多少人不同的心態:
聽聽書中那些浪蕩子所言,那是未被教化調伏的生靈才會有的語言;惜春覺得她是塵緣未斷;而作為一個有社會心的人會覺得,妙玉對寶玉的情愛是可憐而又可悲的;若是從出世間法而言,妙玉的修持則因無高人點撥而出偏,進而前功盡棄,就是憫恤眾生的菩薩見了,終究也會掉淚的。